Photography/ Manchi.
「我現在可以確定地說,我對創作是有信仰的。」
18 年的創作生涯,鄭宜農在她發表了新專輯《圓缺》後,悟出了這個肯定的定論。這是她第五張個人專輯,也是其中的第二張台語創作專輯——《圓缺》講際遇,及相伴而來的缺憾,身為一位追索不歇的創作者,她不斷地自我覺察,摸索著創作之於她而言,究竟是什麼?為了想出一個最好的詞、一個最貼切的聲音,她願意細細雕琢一整天,這個心流的過程對她來說是神聖的,像人生縮影般,在挫敗的必然與成功的喜悅間來回擺盪。
懷抱著對創作的敬意,享受著和創作「框架」的相處,鄭宜農好似與之平起平坐下著一場慢棋,步步運籌。「就像是看到界線的話,就會想衝破它,這是身為創作者都會有的慾望。」就此感受自己在框架裡能抵達的極限,棋盤格的格局既定,如何佈局便是技藝的凝練。


人如何學會語言
小時候沒學好台語,似乎是鄭宜農心裡的缺憾。
2010 年她第一首以台語發表的作品〈莎呦娜啦〉誕生,和楊大正共同譜寫,作為她在電影《眼淚》中飾演角色的出口,「我和角色之間不一定可以互相理解的成分,藉由一首歌很自然地就跨過去了。」電影本身文本多為台語,又欲想相稱角色的江湖氣息,她與台語在音樂上的起點,不出於野心,只因為正好的緣分。
後來她發了個人專輯、組了團,多以華語書寫;再度置身台語語境,得等到 2019 年為《奇蹟的女兒》所寫的〈玉仔的心〉。《奇蹟的女兒》和《眼淚》皆是父親鄭文堂導演的作品,如同冥冥之中的巧合召喚,她和台語最原生的血脈牽引,成為她用以書寫的開端契機。
而後她持續嘗試台語創作,〈街仔路雨落袂停〉、〈深深地〉相繼而來,收錄在取得市場極佳反響的專輯《給天王星》。走到了彼時階段,在思索下一張作品的核心時,她決定以成長背景作為切口,為自己,也為這個語言。


「在語言的運用上,我從小到大都不是一個那麼順利的人,那不如就以這作為主題吧。」在家中她話說得少、感受得多,語言的養成「後天」成分居多。她對作家吳明益在《苦雨之地》的短篇小說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感同身受,寫下了同名歌曲,作為首張台語專輯《水逆》的開篇。
「製作《水逆》時,我曾一度擔心會被框架打敗,因為當我開始做一張全台語的專輯,那個框架是非常剛烈的,但我不是那樣個性的人。」她想寫形而上的事、寫細膩的情感和精神面,可是台語的表達相對具體,曾讓她難以找到純粹去描述感受的詞彙,她嘗試相處後才跟前所未見的框架達到共識,透過創作具體實踐「學會語言」這件事,讓《水逆》最終成為時間裡的行為藝術標本。

問出更好的問題
實與不實,是鄭宜農在《圓缺》裡的重要抉擇,而「缺憾」,則是她給自己的創作框架。「我通常會在很小的事情裡面,感受到很大的東西。」她習慣描寫碰觸的瞬間、吐納的氣息,這一次卻將創作意念灌注在「血肉」、「生命」、「電火」等更具「實」感的詞彙上,「即便如此,這張作品聽起來還是『陰性』的。」
《圓缺》命名來自於月相,月亮對她來說是陰性的存在,「這一顆安靜的、凹凹凸凸的灰色球形天體,它帶來了潮汐,以及我們身體上的變化,紮紮實實地影響著我們的人生,這是我想要在創作裡不斷實踐的精神,用陰性的方式帶來情感,或是衝擊。」
從感受的碎片為起點,生命、時間、記憶成為專輯命題的核心,「近幾年我對於時間流逝覺察到具體的害怕,這是在某個年紀以前還不會那麼認真去體會的事情。」周遭老去的面孔、肉體的脆弱、生命的消逝,在她生活裡逐一昭然浮現,讓她不禁思考如果「離開」倉促到來,還有什麼未盡的言語?死亡意味著什麼?生命又會引領我們走向何處?


我後來發現,我認為的「好的創作狀態」,是我們努力去把心裡困惑的問題問好,所以我開始想要問出「更好的問題」,或是把長期存在的問題寫出來。
於是,大大小小關於「缺憾」的種種心緒與疑惑在作品中浮現,跨度極大,從私我到群體,從肉身的裂口到歷史的裂縫。與韓國創作歌手李瀧合作的〈寬寬仔來到祢的面前〉,她首次在歌裡寫了「神」,藉由與神、與造物主的對話,拋出「人世間為什麼變成這樣?」的疑惑。兩人在創作傾向上迥然不同,李瀧的「外實」與鄭宜農的「內隱」,在歌中如同人與人相遇之際的拉鋸張力,交織成一個無解卻一再循環的問題。
在〈講袂出嘴的彼个字〉,她寫進了自己幾乎鮮少說出口的「我愛你」;還有更多語感先行的詞句靈感,〈未曾準備好〉、〈一寡時間〉皆是先浮現了順口的聲律,才接續延展完歌曲。〈留佇咱的血內底〉則從作家賴香吟的小說《白色畫像》裡窺見了空缺,「那個空缺是我們這塊土地的命運,跟我們這一代人要面對的事情。」「國」的重量在歌中最後落於「家」的柔軟,「我們的『愛』跟『不滿』,常常可能是融合在一起的。」如今,她更懂得如何使用台語去表達原生家庭複雜的情感,也展現出更自如掌握的語感,「希望大家可以聽出來,現在『台語』這個框架對鄭宜農來講不再是不自由的了,身為一個創作者跟語言的關係之間,我漸漸找到了脈絡。」

生命充滿狼狽缺憾,卻也因而美麗
創作上的突破也呈現在作品的聲響,和製作人 Chunho 的合作到了第三張專輯,兩人有各自的野心,鄭宜農悉心雕琢詞曲,Chunho 則用聲場設計與之縱深對話。電子樂的類比聲響,在聽覺上相對理性克制,與措辭濃烈、感性奔放的主題對應,形成了遠近飄忽的違和感平衡。「在這個前提下,我才有辦法寫出這麼重的字,我在寫歌的時候非常謹慎,不想要筆直地只往一個情緒走,我想要空間跟層次。」儘管天性不同,但兩人同樣追求著一種無以名狀的「浪漫感受」。
比如〈未曾準備好〉前後的音軌倒轉,回映詞曲「時間」的命題;〈牽我〉結尾放入聲納的聲音,象徵在靜默的深海之處尋找彼此。〈一寡時間〉則悄悄呼應上張專輯歌曲〈人如何學會語言〉,「當我們找到了自己的時間及語言,也找到了屬於自己、不被外界所影響的核心,心裡面自由的聲音會是什麼?」Chuno 藉由收場的鳥鳴,傳達出對自由樣貌的想像。
曲序最後一首歌〈圓缺〉的尾奏聽感如輪迴,編曲經由 Click 變奏、長笛、短笛、低音號交織出時間迴盪的意象;「在理解了生命的循環與自身的渺小之後,我們要走去哪?」這一分多鐘的聲景裡,她拋出了未來何來的提問。
我們同樣都是有疑問的、平等的、脆弱的、不完美的,但是沒有關係,只要我們牽著彼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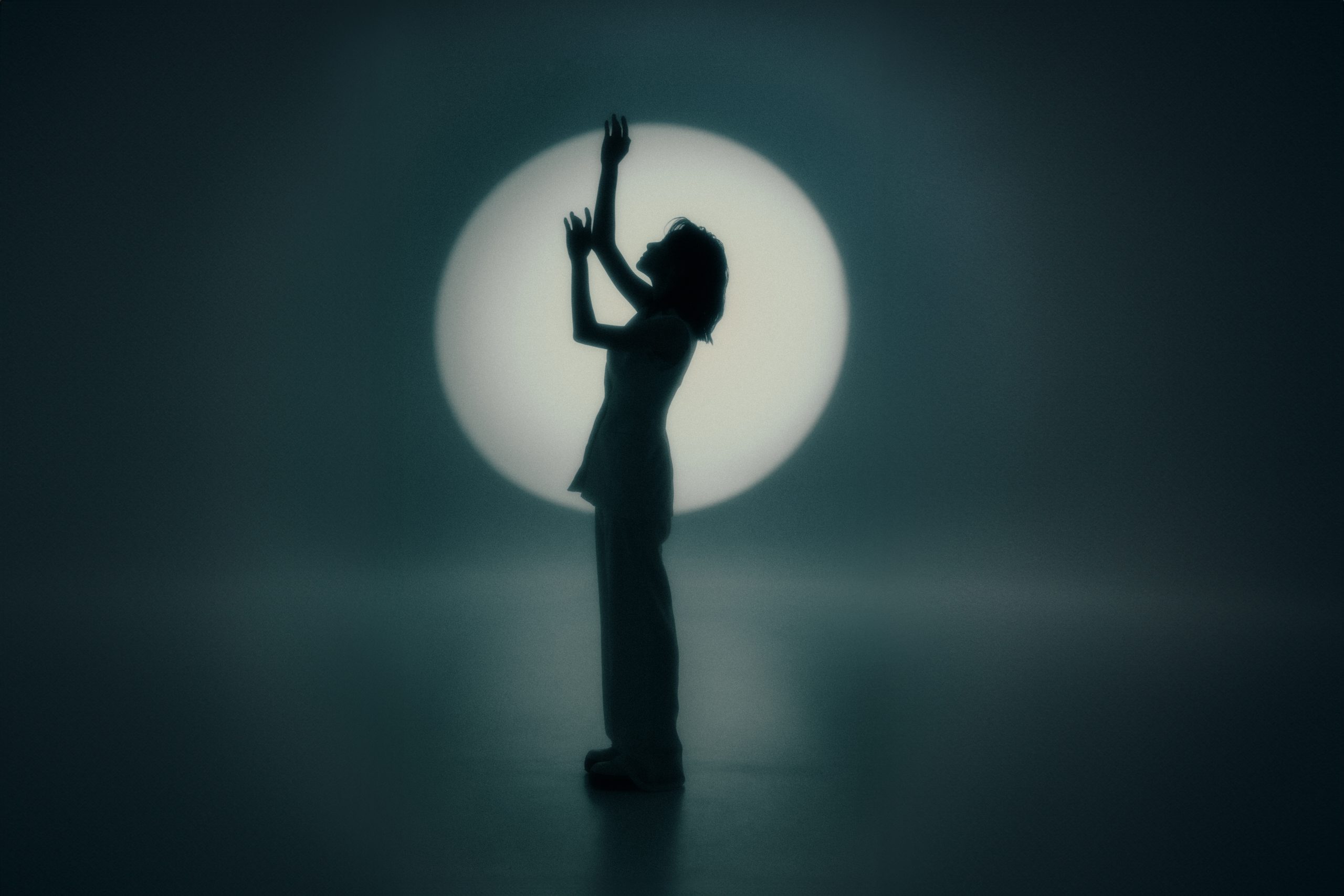
我們同樣都是有疑問的、平等的、脆弱的、不完美的,但是沒有關係,只要我們牽著彼此。
而專輯內幾乎是最後一首完成的〈牽我〉,以最簡單的詞、最純粹的情感鋪寫而成。透過這首歌她描繪出自己心中的理想關係,意象與早前的作品〈光〉遙相輝映。即使整張專輯氤氳著冷冽質地的電子樂,她還是想保有很「鄭宜農」的部分,細膩而真誠,在人與人觸碰的瞬間,能做彼此的良知與燈塔。
感知著創作框架完成《圓缺》,在活到了 38 歲的今天,鄭宜農給了自身缺憾暫時的句點,不確定釋然多少,只能以不斷創作繼續受這世界所牽引,有如時而盈滿、時而空無的月球,忠實反照著某種內在引力。「生命來什麼,我就接什麼。」她知道她要去面對,也明白過程裡會有種種焦灼,欣然以待、學著與不完美共存。一如她與台語之間的關係,本身就是一段名為《圓缺》的自白,她追溯、也織補,與一個語言之間未竟的緣分,用一己之力。


